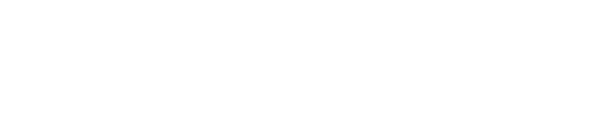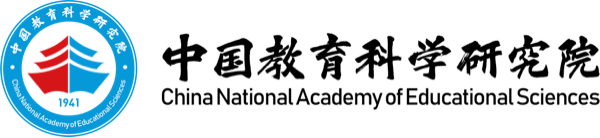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强教必先强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教师队伍建设是关涉多流程、多领域、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从流程性视角来看,教师资源调配是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先手棋。基于学生数量的基础教育师资配置逻辑起点,学龄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及空间布局则成为决定教师资源调配的基础要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度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3,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相较于2000年降低了0.54%。[1]国际上通常将总和生育率1.5界定为“很低生育率”,生育水平一旦降至该警戒线以下后将很难重新回升。[2]202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7.52‰,出生人口规模为1062万,再创新低。[3]不难看出,我国新增人口已经进入下降通道。面对人口变动新格局,着眼教育高质量及教育强国战略实现,以教育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亟须优化基础教育师资调配机制。
一、问题提出
已有研究大多通过人口预测未来学龄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而根据一定师资配置标准预测教师需求。
首先,大部分研究基于人口政策变动(“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放开三孩”)预测教育资源需求中的教师需求变动趋势。该类研究主要聚焦教师资源需求的增加。[4]有研究指出,幼儿园师资缺口巨大,城镇地区尤为明显;[5]有研究基于人口分析,指出小学、高中阶段教育教师资源紧缺;[6]有研究则具体指出,“十四五”期间需补充28.8万名专任教师,“十五五”期间需新增专任教师的数量较大,高达35.5万人,“十六五”时期即2033年后,专任教师需求量开始下降;[7]还有研究综合贯通考虑人口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需求的影响,得出我国学前教育规模先下降、后上升、再缓慢下降,义务教育规模先基本稳定而后缓慢下降,高中教育规模在2021—2026年保持基本稳定,应据此进行教师资源调配[8]。
其次,基于人口新格局及教育强国建设预测各级各类教育师资需求。该领域研究从不同角度设计未来教师配置标准。有研究着眼城乡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差异,基于历史分析和国际比较分别设定城乡生师比和班师比标准,预测未来教师需求,指出教师资源面临不足与过剩的双重矛盾。[9]有研究则对标发达国家生师比和班额标准,采用动态生师比标准,提出2035年小学和初中生师比分别达到13∶1和12∶1。预测结果显示,小学先小幅增长后持续下滑,初中呈现波动起伏,师资数量需求盈缺振幅较大。[10]还有研究着眼教育强国建设目标,通过国际比较和对标,提出未来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师比分别为14∶1、13.9∶1、11.6∶1、12.2∶1。[11]
已有研究既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也拓展了思路和方法。综合而言,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征:一是预测对象从综合教育资源到聚焦教师资源;二是关注学段多为单一学段;三是预测周期多数到2035年。本研究认为,面向未来学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这一基本趋势,着眼于教师资源存量优化和增量配置,需要从学前到普通高中学生人数变化的系统预测,方可找到更科学、更可行的师资优化调配方案。
2050年恰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年,因此,基于最新数据开展基础教育全学段、最长周期的预测研究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基于七普数据,通过经典人口预测方法—队列要素法—模拟2020—2050年我国分城乡各学段适龄儿童的规模和结构变动,充分考虑教师退休等制度性变动情况,进而提出师资调配机制优化思路与对策。
二、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运用队列要素法预测各学段适龄人口,根据城镇化水平设定城镇迁移水平,依据现行师资配置标准预测未来各年度教师需求量,根据教师年龄结构分布情况以五年为周期预测教师退休情况,通过需求量、存量和退休三个方面判断各学段教师盈缺状况。
(一)学龄人口预测
研究选择基础人口、生育水平、生育模式、预期寿命、死亡模式、出生性别比、迁移水平和迁移模式等关键参数,并且各个参数依据七普选择最新数据,对2020—2050年各阶段的学龄儿童规模和结构进行相关模拟预测。各学段毛入学率和城乡学生分布均按照2011—2021年数据对其未来数据进行模拟,根据线性回归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回归系数,拟合出未来各学段毛入学率和城乡学生比例。各学段在校生为适龄人口数量×当年毛入学率。
1.人口预测模型
研究选用队列要素预测法作为人口预测模型。该方法的核心逻辑是年龄移算,将人口按性别和年龄分解为不同队列,再将每个队列的规模变动分解为出生、死亡和迁移三大要素,根据人口参数进行年龄移算来预测每个队列的规模变化,最后将预测时期内每年各个队列的规模加总得到人口总量,同时得到每年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据。(见图1)
图1队列要素法年龄移算(不考虑迁移)
注:图中虚线箭头表示生育,实线箭头表示年龄移算。
队列要素预测法的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Px,t表示t年x岁人口,Lx,t表示t年x岁生存人年数,Mx,t表示t年x岁净迁移人口,SRB表示出生性别比(女婴=100),Bt表示t年出生人口,l0表示生命表初始存活人口,fx,t表示t年x岁妇女生育率,上标m表示男性、f表示女性。
2.参数设定及数据来源
第一,基础人口。本研究使用的基础人口数据来自七普分性别分年龄人口。
第二,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处于超低生育率。[12]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由此估算总和生育率约为1.17。[13]从生育率转变规律、国际经验以及我国人口出生形势来看,未来妇女总和生育率很难大幅回升。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未来妇女生育水平将在1.2~1.3波动变化,并将七普数据中全国及分城乡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作为生育模式参数。
第三,预期寿命与死亡模式。现有研究大多直接使用普查死亡登记数据作为死亡参数,并假定未来死亡水平不变。[14]由于普查数据死亡漏报较为明显而导致死亡登记数据作为死亡参数的误差,[15]以及以固定预期寿命作为参数不符合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事实,本研究以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性别预期寿命为基准,按照联合国预期寿命增速假设的中高速模式估算未来寿命水平,选用与我国人口死亡模式较为接近的寇尔德曼西区模型生命表设定死亡模式参数。
第四,出生性别比。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1.3。[16]从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的变化来看,基本维持在110左右波动,因此假定未来出生性别比保持不变。
第五,迁移模式与迁移水平。根据七普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设定迁移模式参数。参照国家城镇化规划目标和进程速度,设定2035年城镇化率为35%。[17]假定未来城镇化水平呈线性变化,以此推算平均每年增加0.74%,据此设定未来城乡迁移水平。
(二)教师盈缺研判
1.教师需求预测
已有研究或基于国际比较对标[18]或基于综合分析状态[19]等多方考虑提出面向不同年份、不同区域教师生师比标准。但也有研究认为,基于班师比核定教师编制,存在计算复杂、人为或政策影响因素较大,不利于宏观控制;相反,基于生师比的核定方式从宏观入手,直观且操作简单,便于宏观调控。[20]在综合研判基础上,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根据我国教师配置标准制度变迁历程及价值导向,本研究依据以下原则或思路对教师需求进行预测。一是坚持鲜明的政策导向和实践导向,即充分考虑教师需求预测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宜过于繁琐,从国家层面设定统一的生师比标准,地区差异、学校类型差异等暂不考虑在内。二是坚持制度的稳定性原则,未来教师需求预测采用固定的生师比标准。三是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即生师比标准设定不宜过于理想,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条件,特别是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原则性要求。综合以上,本研究将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师比分别定为14∶1、14∶1、13∶1和12∶1。(见下表)
已有预测研究生师比标准表
|
研究者 |
学前 |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
周琴,等 |
13∶1 |
12∶1 |
||
|
梁文艳,等 |
16∶1 |
12∶1 |
||
|
吴瑞君,等 |
14:1 |
13.9∶1 |
11.6∶1 |
12.2∶1 |
2.退休教师估算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中各年龄段教师性别比例,计算各年龄段男女教师人数,基于女性教师55岁、男性教师60岁退休,分别预估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2045年和2050年教师退休人数。
教师现存量以《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年》各学段教师为基数,由预测需求量减去教师基数与教师退休之差计算不同时间各学段教师调配需求。
(三)预测误差检验
将2021年学龄人口预测值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2021年分年龄人口数据进行对照,在所研究年龄段(3~17岁)上误差率绝对值均在10%以内,甚至多数年龄的预测误差绝对值在3%以内(见图2)。根据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AbsolutePercentageError,MAPE)的标准,当误差值小于10%为高精度预测,在10%~20%为良好预测,在20%~30%为可行预测,大于50%为错误预测。[21]因此,本研究属于高精度预测。
图2学龄人口预测精准度检测
三、学龄人口预测结果
总体来看,各级教育适龄人口长远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学段的降幅和趋势存在一定差异,城乡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
(一)学龄前儿童的规模及结构变化
1.学龄前儿童变动呈现出“降—稳—降”的趋势
2020—2050年,我国学龄前儿童规模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降—稳—降”波动式变化。其中,2020—2030年,将从5200余万迅速下降至2900万以下,2030年后,维持在2800万上下平稳浮动,其后从2040年再次下降,降至2050年的2500多万。(见图3)
图3 2020—2050年分城乡学龄前儿童的规模变化
2.乡村地区学龄前儿童降速和降幅均显著高于城镇地区分城乡看,未来十年城乡学龄前儿童的规模都将进入快速下降阶段。2020年,我国城镇地区学龄前儿童为3378万,乡村地区学龄前儿童为1901万;2030年,城镇学龄前儿童降至2239万,乡村降至689万;2050年,城镇和农村学龄前儿童分别下降至1888万和674万。
从绝对规模的差异来看,未来三十年内,城镇学龄前儿童始终远多于农村;从下降速度看,2020—2030年,城镇学龄前儿童下降为33.72%,乡村降幅高达63.76%。由此可见,乡村地区下降更快。
(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规模和结构变化
1.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变动呈现出“稳—降—稳”的趋势
与学龄前儿童的规模变化不同,未来我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规模呈现“稳—降—稳”的变化趋势。2020—2025年,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规模基本维持在1.6亿左右,其后进入下行通道,2030—2040年,降至8500万左右,降幅达到45%以上。分阶段看,6~11岁小学适龄儿童表现出类似的变动趋势,2020—2025年,维持在1亿人以上,在经历数年平稳波动后,从2026年开始明显减少,这主要是由于2017年后“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已释放完全而年度出生人数回落导致的。小学适龄儿童在2035年左右降至6000万以下,其后维持至2050年。同期,12~14岁初中适龄儿童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未来十年,初中适龄儿童规模将出现一个不明显的波峰,从2020年的5021万缓慢增长至2026年的峰值5585万,然后开始下降,2031年降至5000万以下,2035年以后降至3000万左右,其后维持在2800万上下直至2050年。(见图4)
图4 2020—2050年中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规模变化
2.城镇地区适龄儿童先增后减而农村地区先快速下降后轻微回升
分城乡看,义务教育适龄儿童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城镇地区,未来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将先增后减,从2020年的9503万增长至2024年的峰值10196万,其后较长时间呈现下降趋势,2032年降至8000万以下,2050年进一步下降至6234万。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适龄儿童表现为先快速下降后轻微回升的变化趋势,从2020年的6392万快速下降至2039年的1808万,后轻微回升,2050年回升至2326万。
分阶段看,城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差异更加明显。具体而言,城镇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呈现先增后降再平稳的变动趋势。从2020年的6578万增长至2023年的6990万,随后开始进入近20年的下降阶段,在大约2040年降至4200万左右,并维持至2050年;初中适龄儿童将继续保持十年左右的缓慢增长,从2020年的2925万增长至2029年的3591万,平均每年增加74万,其后开始数年的较快下降,2035年降至2500万左右,随后降速放缓,2050年降至2131万。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的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农村小学适龄儿童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未来十余年降幅明显,从2020年的4296万降至2036年的1187万,降幅达到70%以上,平均每年减少194万;初中适龄儿童则呈现“稳—降—稳”的变动趋势,2020—2025年维持在2000万以上波动变化,随后开始较明显下降,2033年降至1000万以下,2039年降至528万,其后略有回升,2050年回升至750万左右。
(三)高中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
1.高中适龄人口规模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020—2050年,我国高中适龄人口的规模将先升后降,与同期学龄前儿童(降—稳—降)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稳—降—稳)的变化趋势明显不同。2020年,高中适龄人口规模为4427万,未来将保持增长态势直至2029年达到峰值5581万。随后,高中适龄人口开始减少,2033—2038年是该群体规模迅速下降的时期(对应2018年后出生人数减少),从5137万降至3243万,降幅达36.88%,平均每年减少380万。截至2050年,高中适龄人口在2800万左右。(见图5)
图5 2020—2050年中国高中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
2.城镇地区高中适龄人口呈现波浪式变化,农村地区则表现为“升—稳—降—稳”
分城乡看,高中适龄人口的规模变化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点。在城镇地区,高中适龄人口呈现波浪式变化,未来历经数年的短暂下降后出现较明显上涨,在2020—2030年维持在3600万上下高位波动,其后再次下降,2035年降至3000万左右,2045年后在 2100万~2200万波动。在农村地区,未来三十年高中适龄人口的规模变化可以总结为“升—稳—降—稳”。2020—2025年,农村高中适龄人口显著增加,从1200万增长至 2030万,其后至2030年一直维持在1900万左右,2030年后开始明显减少,在2042年降至最低点493万,随后在500万~600万波动。
四、教师调配需求研判
在人口预测基础上,综合考虑教师存量基数、退休变动等情况,特别是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以及人民群众对优化教育资源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对未来各学段教师调配需求研判。总体而言,初中及以下学段教师重在存量优化,高中教师则需要持续配置增量。
(一)幼儿园教师需前期调存量与后期配增量
数据显示,2021年,幼儿园生师比为15.06∶1,城镇和乡村分别为14.57∶1和17.56∶1。对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国家学前教育生师比长期维持在14.4∶1~15.3∶1[22]可知,全国范围及城镇地区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连续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学前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3]专任教师从2010年的114多万增长到2021年的319多万,增长近2倍。从全国来看,学前适龄儿童呈现出“降—稳—降”的变动趋势,2025年前幼儿教师需重在优化存量,后期随着存量教师的退休而需加强增量配置。就退休情况而言,2021年,全国幼儿园教师74.73%为35岁以下,45岁以上教师仅占25.27%,因此,2040年后才进入退休高峰年段,并进入增量配置阶段。(见图6)
图 6 2025—2050年全国幼儿园教师退休、需求及调配方向
(二)小学教师需以长期调存量为重
2021年,小学阶段生师比为16.33∶1,已经低于国家规定的19∶1。根据本研究设定的小学生师比14∶1进行测算,2040年前需优化存量,2040年后进入增量配置阶段,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再到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教师补充始终是国家战略重点,从“特岗计划”到“公费师范生政策”到“强师计划”再到“优师计划”,政策在全面补充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从全国来看,就教师需求而言,因“二孩政策”“三孩政策”适龄儿童增加从而使2025年需求量最大,随后下降,2035年降至最低,然后小幅变动维持至2050年。就退休情况而言,呈现比较稳定的趋势,2045年退休人数最多。就调配需求而言,因适龄儿童减少,小学教师长期存量优化,直到2040年及以后,因存量教师大量退休后需加强增量配置。(见图7)
图7 2025—2050年小学教师退休、需求及调配方向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差距以及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人口不断涌向城镇地区,造成当前“城镇挤、乡村空”的现象。[24]2021年,城镇和乡村小学生生师比分别为17.40∶1和13.24∶1,均已高于国家规定标准。因此,2040年前,城镇小学教师更需要优化存量,2045年后,城镇小学教师因退休人数不断增加而需要加强增量配置。
(三)初中教师需在调存量基础上配增量
2021年,初中生师比为12.64∶1,已稍高于国家标准。按照初中生师比13∶1测算,从需求量而言,2025年最大随后持续下降,其中,2030—2035年降幅最大,之后保持稳定。从退休状况来看,2035年前逐年增加,随后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就需调配需求而言,2025年及以前重点以存量优化为主,2030—2035年,教师需求持续下降且降幅较大,2035年后,增量需求再次持续增加,其中,2045—2050年增量增幅较大。(见图8)
图8 2025—2050年初中教师退休、需求及调配方向
从城乡来看,2021年城镇和乡村初中生师比分别为12.83∶1和11.40∶1。2025年及以前城镇地区初中教师需一定增量配置,而乡村教师需加大存量优化。2030年,城镇地区需要大幅增量配置,而乡村地区呈现基本平衡状态,2035年,则出现城乡均需优化存量,特别是城镇地区教师,至2050年,城镇和乡村均需适度增量配置,城镇地区需求高于乡村地区。
(四)普通高中教师重在配增量
2021年,普通高中生师比为12.84∶1,稍低于国家标准。根据本研究设定的普通高中生师比12∶1进行测算,从需求量来看,因2030年前后是普通高中适龄学生最多的时间段,2030年是普通高中教师需求量顶峰,随后下降,2035年需求量降至最低,2040年持续下降后至2050年维持基本相当状况。从退休状况来看,鉴于当前普通高中教师年龄分布较均,从现在至2050年,退休数量变动幅度较小,呈现稳步正常退休状态。从调配需求来看,2025年增量配置需求最大,随后下降,2035年降至最低,2040年有所回弹,随后至2050年维持平稳状态。(见图9)
图 9 2025—2050年普通高中教师退休、需求及调配方向
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地区教师变动趋势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乡村地区普通高中教师需求量持续下降,2040年降至最低,随后维持到2050年。
五、师资调配思路与对策
教师资源调配不仅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事项,配得是否到位、调得是否合理关系教师队伍的稳定及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教师需求持续下降且存量总体饱和的情况下,更要进行科学调适。教师队伍要保持适度的人力更新,同时教师资源增量配置也是承接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未来基础教育师资调配,应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导向,以满足学生发展多元化需求为价值取向,促进教师资源配置从简单量的调配到岗位结构、学段结构和空间布局的综合优化。
(一)优化整体+局部多向适应的教师总体配置机制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基于现有中小学教师配置标准,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配置已实现省市县三级达标,[25]但教师资源调配不仅仅要实现总量足,更要实现结构上的合理,即不同学段、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等多元结构合理。且多方研究显示,中小学教师配置不够、不足严重影响教育教学改革的正常运转和运行;[26]基于生师比单维指标的教师编制核算方式不切合学校教学的班级组织形式对教师的需求;[27]政策上超编而实际缺编、结构缺编问题严重;[28]不符合小规模学校的师资需求;[29]乡村学校“结构性缺编”,城镇大规模学校“总量性缺编”[30]以及实践中存在城乡不均衡、校际超缺员并存、学科间余缺不等的现象,特别是音乐、体育、美术、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专任教师严重不足[31]。这些问题足以反映当前教师配置供给机制难以真正满足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即便学龄儿童下降之后,这些问题也难以自动解决,而是需要从根本上优化配置机制。面对学龄儿童减少这一总体和长期趋势,首要是从根本上优化基础教育教师配置总体供给机制。
现行教师配置标准难以观照教育改革发展的多样态存在,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固定编制与机动编制相结合的教师配置供给机制。固定编制实行基于学校类型的差别化标准,由编制部门核定下拨。机动编制在固定编制基础上上浮10%,实行学校申请—区县审批—年度动态调整制。一是针对规模适中(小学500人以上,初中1000人以上)、教师工作量达到标准、能够开足开齐课程的学校,按照现行标准核定和配置教职工。二是针对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调研发现教师周平均教学工作量为16~22节,比工作量标准平均超出约为1/3工作量),按照现行小学班师比1∶2,需按照班师比1∶2.4核增编制。三是针对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教师周教学工作量为18~24节,比非寄宿制学校教师的12~16节多出1/3到1/2工作量),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现行师生比1∶19、1∶13.5和1∶12.5基础核增编制,根据工作量超出部分应将生师比调为14.3∶1~12.7∶1、10.1∶1~9.0∶1和9.4∶1~8.3∶1。
(二)完善分级+分类双向轮动的教师岗位设置
数据结果显示,基础教育师资配置的重点大部分在于存量优化。如何将教师资源优化配置起来,细化岗位门类设置是基础。2022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作出全面规范。但这一意见重点对教师岗位分级设置进行规范和管理,着眼教育教学改革需求,未来教师岗位设置还需在分类上下功夫。一是明确教学岗,主要承担国家课程规定的各个学科教学、教研、科研,专心做好学科教学与研究。二是设立教辅岗,主要辅助教学岗教师做好学生信息收集、通知发放、家校沟通等系列准备。三是明确管理岗,面向学校课程、教学、德育、人事等各个领域的日常管理,确保学校日常运转、内涵发展及质量提升。四是设立学生发展指导岗,为全体学生在理想、心理、学业、生涯、生活等方面提供课程活动、团体辅导、个别指导等一系列服务。数据显示,2021—2022年,美国全国学生与学校辅导员比例为408:1,且小学配比高于高中配比。[32]芬兰面向7~9年级学生设立专职学生发展指导顾问岗位,该岗位需经国家相关法律认定资格的全职带薪工作人员,目前,芬兰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约为250:1。[33]我国也已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提出对学生发展指导的要求,地方也做了实践探索,如有地方规定每所高中学校至少配备1名生涯规划教育专职教师。[34]当然,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畅通各类岗位教师发展通道及配套制度。
(三)创建转岗+跟岗相结合的教师跨学段流转机制
数据显示,未来不同学段教师资源盈缺程度不一,其中学前教师和小学教师富余周期和数量位居前两位。为此,应有效应对低学段教师资源富余的现实情况,做好学段间衔接。一是探索教师跨学段转岗制度,满足不同学段师资需求。通过开展专项培训、在职学历提升等系统化培养,经过一定专业能力考试与实践考核,有意愿、有基础、有能力的小学教师向幼儿园教师和初中教师转岗,实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在学段间高效配置。二是探索开展教师跨学段跟岗观摩制度,做好学段科学衔接。在县域内、学区内、集团内,试行每个学期开展一定时间深入到衔接学段跟岗学习交流,了解低级或高级学段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方向、学生的教育准备、可能存在的问题或着重提前铺垫的知识、能力和习惯等要求,以便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做好铺垫或衔接。各地可根据不同学段教师资源情况,开展不同方向的跟岗交流。如2021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双向衔接和系统推进的基本原则,做好幼小衔接。
(四)深化县域+城乡双协调的教师城乡空间交流机制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农村人口降幅和降速均高于城市人口,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将继续向城市流动。为提升教师资源配置效率且促进教育公平,教师城乡空间交流机制亟待创新并切实提高实效。一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实现教师资源在县域内合法合理交流。深化教师编制统筹、优化教师交流轮岗程序、强化教师交流轮岗多元保障,确保教师资源在县域内有效统筹。二是探索建立城乡教师专业互助制度。实行乡村教师到城区学校跟岗学习或城区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服务的基本制度,将到城区学校或优质学校跟岗学习作为未来乡村教师培训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切实从根本上提高乡村教师专业素质,提升其为师从教育人的热情、投入和成效。此外,将指导或引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城区教师专业晋升的激励条件,优化过去将城区教师到乡村学校开展一定期限的教育教学服务作为优先条件。
来源 |《教育研究》2024年第11期
作者 | 李新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实验协作处研究员)、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